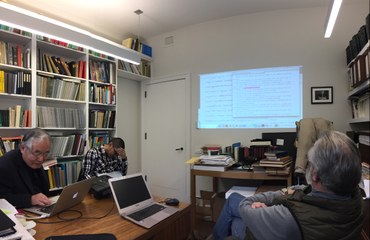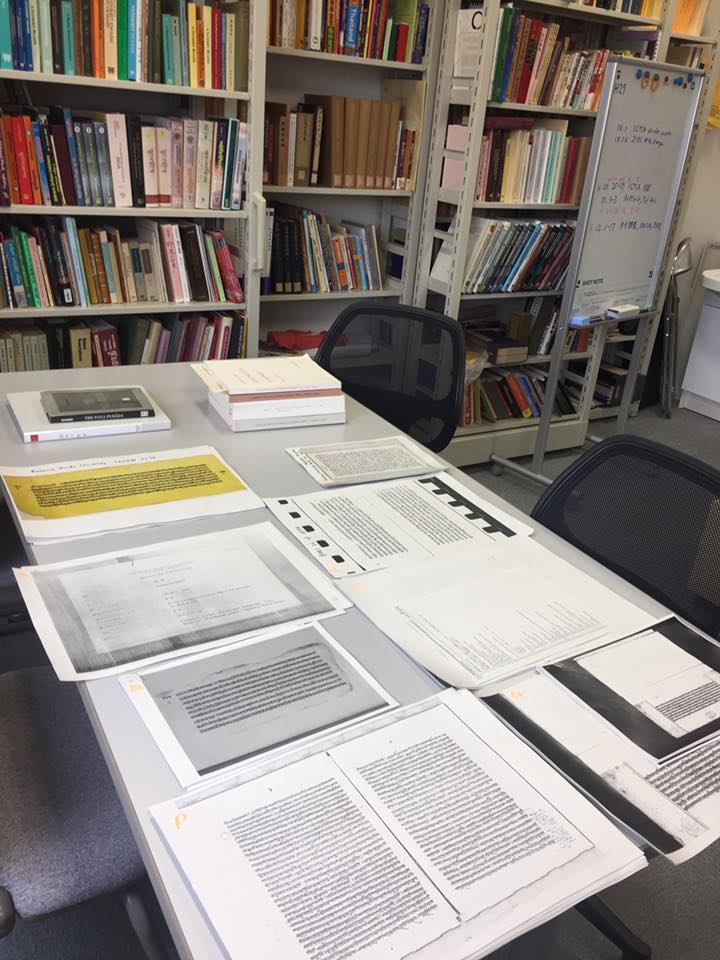中港兩地雙方矛盾--過去、現在與未來
中港兩地雙方矛盾--過去、現在與未來
生活在北京四年,作為一個香港出生的人,在國內一般被認定為香港人,體會了不少社會普遍對香港人的偏見。造成這些偏見,大概因於國內的教育和媒體,還有各種特殊的「國情」。同樣地,香港人對國內同胞,儘管回歸二十多年,中港經濟接近一體化,還是抱著各種成見和誤解。就這個話題,讓我分開三個題目說:一)歷史觀、二)身分認同和歸屬感、三)價值觀和未來抱負。
一)歷史觀
中國人就是中國的人。然而不同的中國人對中國的理解,差異甚大。每個中國人都大概有他認為理所當然的見解,中國便是中國,難道有不是中國的中國嗎?答案是有的,視乎是哪個時代,跟誰說,還有什麼語境。
你的中國不一定是他的中國。
先說「中國」,什麼是「中國」?從三皇五帝到新中國可以說成中國嗎?元清兩朝都是異族統治的,也算中國嗎?中國是地域的概念,還是民族、政治的概念?再說現代、國共兩黨建立的中國,雙方互不承認,誰說的作算?共產主義能打造一個全世界華人都能接受的中國嗎?
歷史像個黑盒子,從多角度不斷探索,出現各種不同的見解。有些見解無法說清,但不能說這就代表公婆有理,所有見解都要平常心接受。非也!皆因有些見解是錯誤的,需要全盤否定。有些見解含主觀因素,需要釐清。要分辨是非,先要認識歷史。然而,中港兩地一般人對中國的歷史,特別是近代史的了解都是異常膚淺,有時候幾乎近於無知!
為什麼?
說歷史的人也好,就算是一般說話的人也好,發言背後都有目的。教科書是國民教育的工具,需要強調有利培育國民素質的內容,敏感和具爭議性的話題只能留給政治家和學者議論,免得迷惑大眾。坊間書本和雜誌要求銷量,所以內容傾向誇張煽情,吸引讀者,並不求實。現今網絡開通,大家都敢說真話了,但真話卻被噪音所掩蓋,虛假消息氾濫,孰真孰假,非明眼人不能辨之。
國內的中國人一般把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跟「中國」視為等同,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實,這是有理由的。從地域和人口來說,中共政權全面掌控「中國」。國外人所謂的「中國」(China)也就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。中文,即「Chinese」也就是「普通話」,這是中共政府的主張;其他中國人說的語言,不管其歷史背景,都淪為「方言」。國內的中國人把中國大陸視為中國的「母體」。所以香港回歸,是理所當然的回到「母親的懷抱」。
對香港人來說,從情感層面來說是個「肉麻」的說法,事實上這也是極為片面的歷史觀。除了小部分的原居民,第一代的香港人都是來自內地的。但當時內地的共產黨,還是被看作為受外國勢力操控的非法組織。香港人在共產政權成立以前在香港植根,所以沒有理由會認同共產政權。他們理解的中國是推翻清帝制以後,國民政府建立的新中國,並不是中共的新中國。儘管不是所有香港人對國民黨有歸屬感,但沒有香港人會否認孫中山是國父,或至少是個民族英雄。遺憾的是,國父的國,並不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。國民黨政權統治的中國,稱之為「中華民國」。不過,現在「中華民國」的領導接受了現實,不再以中國之名而爭鬥,退而自稱「台灣」。香港人心裏的中國,可以說在歷史消失了。
記得小時候我在香港的天主教小學上學,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,但沒有人跟我說過辛亥革命後國共之間的矛盾。大家只知道內地兵荒馬亂,妻離子散,大家逃命來到香港,保了一命。大家都知道共產政權是後來才出現的,依靠蘇維埃外國勢力崛起,而且從土改到文革給中國人帶來不少痛苦,各種政治運動,死了不少人,對中國文化嚴重破壞。「共產黨」一詞,聞之色變。國內人不會說這些,但在香港都是常識。在香港人眼中,中國政府對言論的管制是虛偽和不文明的表現,而內地人避而不談並支持共產政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。
在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出生的中國人,把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看為理所當然的「中國」,在非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出生的中國人的眼中,卻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實。那麼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?
四年北京的生活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。我發現香港人心目中的「負面中國」是停留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。記得小時電視播放江青審訊一幕,給我帶來陰影。還有各種以文革為題材的電影,讓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個蠻荒世界,到處都是壞人。事實上,國內的中國人已經把那個時代的事情忘得幾乎一乾二淨,我個人認為可能忘得太乾淨,不過中國人畢竟需要往前看。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斷在進步,我認識國內不少讓我敬佩的人,特別是從事公益活動和民間社會活動的,他們抱有一種香港人中少見的理想主義和無私奉獻的情懷。而且國內的年輕人十分勤奮, 面向世界。反之,很多香港人沒有認真積極了解國情,還在沈溺過去的光輝歲月,不知不覺的在各方面都給內地同胞趕上了。
二)身分認同和歸屬感
內地同胞也好、港澳台同胞也好、甚至海外華僑,只要接受過中文或華語教育,都不會否認自己為炎黃子孫,龍的傳人。在國外,大家都被稱為「Chinese」。「華人」、「唐人」、「漢人」也好,大家都能接受。然而說到「中國人」,為什麼有些人不能接受?
在國內的時候,不少人問我為什麼香港人那麼抗拒中國大陸?為什麼身為中國人,不能接收中國人的身分?什麼辦法能提高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?
其實這些問題,出發點都有多少偏差,而這個偏差很大程度上基於不同的歷史觀。
教科書可以改寫,甚至歷史也可以改寫,但經歷過歷史的人不能忘掉歷史,更不能完全改變歷史所帶來的現實。
首先,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抗拒中國大陸。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已經接受了現實,那就是香港回歸,還有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擁有香港統治權的現實。所以所謂「港獨」等極端言論完全是無稽之談,除非中共政府做出令香港人極為反感的舉動,「港獨」根本不可能得到大眾的支持。然而,中共官方言論還有一些國內同胞把中國甚至自己看成母體,把香港人看成失散多年,回歸母體的孤兒,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。
中共政權對香港人來說是個陌生的政權,儘管近年國際形象大為改觀,很多跟中共政權永遠掛鉤的負面歷史,像文革和六四,不管在香港人心裏,還是全世界華人的集體記憶中,都是不能磨滅的痛苦記憶。香港人當中,有不少是逃難來到香港的,有一些經歷過國共內戰,也有一些經歷過國內土改、勞改和各種改革政策帶來的不幸,對共產主義抱著完全不信任的態度。這也不能怪香港人。事實上,共產政權統治的國家,大都出現過獨裁主義、內部屠殺清洗和嚴重貪污腐敗等問題。香港人在回歸以前,根本沒有欠過共產中國的恩情,而且有一部分上一代的香港人是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來到香港的。與其說回歸祖國,事實上只是政權轉換,香港人本身並沒有發言權。所以要改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,就跟要改變國內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一樣,不是要做某一件事,而是需要時間的累積,還有視乎中國形象的改變。
為什麼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願意當「中國人」?
因為往往自稱「中國人」的「中國人」把自己看成大,把香港人看為小。特別是北京人,經常有香港屬於「咱們」中國,所以「你們」香港人屬於「咱們」的邏輯。而且有些國內同胞,對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抱有嚴重的誤解,認為香港人受了英國人的殖民統治,心都歸向了紅鬚綠眼的洋人,對本是同根生的中國人卻嗤之以鼻。
崇洋並不是香港人獨有的現象。不管中還是港,大家都會穿洋服,吃西餐。記得第一次會內地,驚訝的看見耕地的大叔也穿黑西服幹活!反之,香港人從來沒有經歷過像文革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鬥和排斥,所以中國文化和傳統的價值觀在香港社會能夠植根。沒有香港人會因為受過殖民統治後而把自己認同是個英國人。實際上,英政府也從來沒有灌輸過這種思想。政府機構和一些公共機關會有英女皇徽號或肖像,但除了警察外,我沒有聽說過香港人需要向英國宣誓。我在港接受的九年「免費教育」,沒有隻字牽涉國民教育,效忠英國等說法。歷史課分中史和西史,後者即是世界史,沒有特別宣揚英國怎樣偉大,反而學習殖民主義怎樣改變了世界,還有中國怎樣演變成現代的局面,實事求是,也沒有特別刻意貶斥中國大陸。
語言方面,英語是外語,大家說的都是廣東話。廣東話是從古代漢語發展出來的現代漢語,保存了入聲,四聲俱全,讀唐詩宋詞時朗朗上口,比屬於官話語系的北京話歷史要長久得多。對香港人來說,普通話是外地方言,幾乎是外語。在內地接受教育的中國人,把「普通話」看為文明的標誌,把說方言看為落後,不文明的舉動。這是官方的見解,也是主觀的偏見。其實北京話也好,廣東話也好,都是語言,本來沒有高低之分。大家都希望說自己的母語,這是大家應有的權利。不過要解決語言問題,共通語是必須的,而香港人也接受了必須學普通話的現實。其實,這跟大家接受了必須學英語一樣,並不代表香港人放棄保衛自己母語和其他傳統文化的權利。
總的來說,怎樣提升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?第一,中國和香港在不同的歷史認知和一國兩制的管治狀態下,意識形態畢竟有分歧,不能完全達到共識,與其強迫對方「歸順」,不如求於君子和而不同。有些香港人對共產政權沒有信心,認為「中國」強權統治,沒有包容之心,一黨專政,不能邁向民主,所以寧可移民。事實上,中國大陸也有不少人跑了,甚至不少中國高官近親,都是拿著美加澳等外國護照的。所以歸屬感這個話題,不應該針對香港人而說,而是面向所有中國人來說的。在任何國家要提高國民的歸屬感,國民必須對其政制和政權抱有認同感。不能反映民意,甚至違反民意的舉動只能破壞這種情懷。
試想清初的明末遺民,怎樣面對一個陌生和外來的政權?
香港人從來沒有接受過馬列主義的薰陶,也不願意去學習這一套連俄羅斯也放棄的思想。大部分香港人看不到毛澤東的偉大,體會不了他的魅力。國內近年的紅色旅遊,緬懷毛主席等舉動,在香港人眼中跟北韓人民崇拜金正日的模樣沒有區別。 國內人把共產黨看成父母一樣,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,不管受過什麼打擊或挫折,大家多多少少都受了共產黨的恩。香港人沒有這份共同歷史,沒有這種情意結。
所以中國要提升香港人對他的歸屬感,只有一個辦法,就是不斷提升自己的形象,讓「中國人」對「中國」感到自豪。到時候不管是香港人,就連其他地方的人也盼望成為中國人。
三)價值觀和未來抱負
中國人在國外多少受到欺凌,這是事實。
每次提到這個話題都讓大家氣憤,所以最好避而不談。
有人說這是因為清末以來帝國主義,鴉片戰爭帶來的一大堆不平等條約,讓中國人飽受凌辱,大損民族自尊。我認為並不是。日德兩國二戰後從戰敗國的廢墟冒起,沒有人因為他們戰敗而說看不起他們。
日德兩國經濟和科技發達,固然大家不敢輕視,然而讓人青睞,並且讓其國民驕傲的並不完全是硬件配套。同樣重要的是文化、文明等「軟實力」。
我在日德兩國都長時間居住過,深深體會到其國民對中國人的偏見。簡單的說,他們看不起中國人不是因為他認為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,或者是中國人窮。不少德國人和日本人拼命學習漢語,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國未來的經濟實力。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是因為他們覺得中國人沒有文化。
什麼是文化?
我想人的肉體是硬件,文化就是他的操作系統。有些操作系統十分優秀,有些就是爛,沒辦法。
中國人的文化是什麼,看一下中國人排隊的模樣,還有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衛生情況,就可以想像到大家對中國人抱有什麼看法。很多中國人不理解國外人的偏見,往往認為對方刻意中傷,以偏概全的把一小部分人的不文明舉動等同於整個中國不文明。
不過中國人也好,香港人也好,就跟德日兩個國家比較而言,整體的國民素質都是偏低的。從禮教、思維的敏銳、文化的素養各方面來看,中國人都有很多欠缺的地方。
然而欠缺了什麼?
每次在不同國家體驗了當地的多元文化活動,中國環節往往令人感到尷尬。隨便問一個留學生說一下自己國家的文化,德國的說作曲家的貝多芬、哲學家的尼采,日本說武士道、動漫。中國的能說什麼?孔子的論語、還是道德經?還是李小龍,少林功夫?中國人有什麼能讓人感動的「軟實力」?
我在日本曾經展出一些書法作品,還有舉辦過一些古琴雅集。參加者竟然稱讚我熱愛日本文化。我幾乎暈倒的說這本來都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傳統文化。中國人沒有好好發揚自己的文化,就連端午節也被韓國申報為無形文化遺產,之後才後知後覺的抗議。這不要怪別人佔有自己的文化,只能怪自己。這不單是國家政策上的問題,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對自己個人文化本位的定位。大家願意花時間認識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的歷史嗎?跑步上健身館還是打太極?讓孩子學習鋼琴還是古琴,水彩還是國畫?
一些中國人也好,香港人也好,往往有一個妄自尊大的想法,認為自己來自一個故遠流長的民族,具有與生俱來禮儀之邦的美德。實際上,新中國只有六十年的歷史,所謂五千年的華夏文明,現代的中國人除了漢字和漢語以外,繼承了多少實在是個大問號。香港人就更不用說了,破碎的歷史觀根本建立不出一個讓自己自豪的身分認同。民國時代蔡元培、胡適、林語堂等都是學貫中西的學人。中國現在趕緊製造軟實力,全世界炮製出多少個孔子學院,只能當語言學校和官方宣傳機構,起不到像歌德學院、法國文化協會等所發揮的效果。這是中國高層智囊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個人經驗而言,我是到了國外才意識到發掘自己文化基因和遺產的重要性。文化需要細心繼承和培育,功利的說是長線投資。二十世紀給中國文化帶來巨大的衝擊,傳統的文化遭受遺棄,甚至破壞。就談古琴,多少人連琴和箏都不能分辨,學鋼琴的是百萬計,學古琴的是百還是千?根本沒法比。日本書道的認真,中國人根本不能想像。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流派,出版書刊,而且可以像空手道的考試、幾級幾段的算。
我在京都跟一位老先生臨摹智永千字文,花了四年時間,每週正座蓆上,行楷兩款幾個字幾個字的,大大小小,老師的細心和耐性實在令人感動。日本人吸收了大量唐宋以來中國最優良的文化傳統,並加以改良提升,在西化的過程中沒有放棄自己的本位。
反之口說愛國,但沒有付諸行動的中國人,盲目追隨外國潮流者居多。現代的中國人和香港人在這方面都需要反思。
放棄文化本位的後果就是失去文化主導的能力,永遠追隨在別人的尾巴。時裝什麼潮流,要看法國。教育什麼潮流,要看美國。藝術什麼潮流,要看歐美。就連娛樂什麼潮流,也要看日韓。
自己底氣不足,怪不得遭別人看不起。
結論是什麼?
中港雙方矛盾,由於各種歷史原因,很難一時作出解決。強行推動一些不成熟的政策,只會帶來反效果和傷害。大家歷史觀不同,身分認同有一定的出入,價值觀不一,這是一個多元社會不能避免的。中國人對待香港人要有多一分的包容,不要隨便亂扣帽子,把所有香港人認定為一個模樣。特別是要認識香港人思想比國內人要自由,一直以來沒有民族和政治包袱。
同樣香港人也需要更努力去認識中國,彼此尊重。畢竟中國不斷的往前跑,都在改變。我相信香港人需要思考如何在中國的發展軌跡上發揮更大的作用,而中國亦需要思考如何給香港人提供這個空間。在這一方面,在政策上必須建立一個普遍接納,並且互相信任的溝通平台。
更重要的事,也就是作為一個學人的願景,就是希望中國人能如何團結,思索怎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發揮正面的作用,對未來地球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作出貢獻。